文圖◉林昌華
新阿姆斯特丹(Nieuw-Amsterdam)是1624至1664年間美國紐約的舊稱,顧名思義,此地在英國治理前曾是荷蘭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荷蘭治理這裡的時間與治理台灣的時間幾乎重疊,有別於治理台灣的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ingh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治理新阿姆斯特丹的是成立於1621年的聯合西印度公司(Geoctroyeer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然而,從宗教層面看,兩地皆是荷蘭改革宗教會的宣教地區。如果說17世紀荷蘭在台灣的宣教是營利組織、宗教組織及原住民族互動的結果,那麼荷蘭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宣教工作也是類似的情況。
宣教工作失敗
東印度公司於1602年設立後,荷蘭人除在東印度地區進行資源和土地擴張,也將觸角伸往北美洲。英國探險家亨利.哈德遜(Henry Hudson)本欲尋找傳聞中通過北極圈至亞洲的東北航道(荷蘭觀點),卻於1609年意外登陸今天的美國東北地區,當地出產大量的毛皮和優越的地理戰略位置,因而成為荷蘭人追求貿易利益及抗衡西班牙的另一重要據點。荷蘭人不僅成立西印度公司,在當地建立新尼德蘭(Nieuw-Nederland),更在哈德遜河河口建立新阿姆斯特丹作為經營殖民地的灘頭堡。
由於荷蘭改革宗教會對成立西印度公司出力甚多,公司某些經營策略無可避免受到教會影響,成立不久就派遣傳道人前往北美洲。儘管傳道人迅速派駐當地,但教會在北美洲的宣教成果卻沒辦法和東印度地區尤其是台灣相比。1643年,牧師尤羅伯(Robertus Junius)宣教14年後返回荷蘭之時,台灣已經有5400個原住民受洗,教會學校也已成立七年,教育許多原住民少年。此外,尤羅伯挑選蕭壠社和附近部落的優秀青年約50名進行師範教育,畢業後成為「學校教師」(schoolmeester)。為了深化教育,他編寫至少三篇簡短的教理問答作為信徒受洗前的教育及平時教育之用,並另外編撰一篇長篇的教理問答作為訓練教師之用。在新尼德蘭服事的荷蘭傳道人對印第安人的宣教遠遠無法望其項背,以致最後一任長官彼得.史戴佛桑特(Petrus Stuyvesant)在1650年的《新尼德蘭報告書》(Representation of New Netherland)中反省宣教工作的失敗時,表達深刻的遺憾:
我們現在覺得羞愧的是,我們是否曾經努力將過去為我們帶來快樂、現在帶來巨大利益的福音分享給印第安人呢?我相信在最後審判的日子來臨之時,他們將要站起來指謫我們為他們帶來的傷害。

兩公司異同
荷蘭宣教師對接觸印第安人的經驗,在目前可見的報告書中皆是負面評價,以致他們宣教的態度也相當消極。然而,靠近海岸的新阿姆斯特丹與位於內陸的阿爾巴尼(Albany)卻有截然不同的做法。在新阿姆斯特丹,幾乎可說沒有任何宣教活動;在阿爾巴尼,第一位在當地服務的牧師約翰內斯.梅嘉波蘭斯牧師(Johannes Megapolensis)能使用摩霍克語(Mohawk)和印第安人溝通,和他們建立友善的關係。第一位印第安人受洗,是在荷蘭人結束治理後20幾年的事。
台灣和新尼德蘭分屬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治理,從商業與政治的角度來看,或許把兩者相提並論的理由相當薄弱,畢竟兩公司特許範圍不同,治理公司的制度也不同,殖民地環境差異也相當巨大,然而,對基督教歷史研究者來講,卻不是如此。首先,兩者時間上幾乎重疊,荷蘭治理台灣是1624至1662年,治理新尼德蘭是1624至1664年,幾乎同時進行。再者,兩公司同樣屬於荷蘭改革宗教會成員。因此,比較兩地政治與宣教歷史紀錄,可發現以下相似點與相異點:
相似點
1.1624年東印度、西印度兩公司開始在兩地殖民時,皆沒有大量移民。當荷蘭最後失去統治者地位時,在台灣或新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均不超過千人。因此當超過十倍的中國人或英國人攻擊時,投降是無法避免的結局。
2.兩地都沒有成立中會。兩地傳道人大部分是由阿姆斯特丹中會考試、封牧及派遣,傳道人彼此有什麼爭論,也都是由阿姆斯特丹中會調解。
3.儘管宣教成果差異極大,兩地都有傳道人努力對原住民宣教。當時,於新尼德蘭服事的首任宣教師、牧師約拿斯.米凱琉斯(Jonas Michaelius)也曾努力學習摩霍克語;約翰內斯.梅嘉波蘭斯不僅熟悉摩霍克語,還開放自己的家讓原住民過夜;即使是對異族宣教不積極的牧師埃弗拉杜斯.波哈篤斯(Everardus Bogardus),遭摩霍克人敵視時仍竭盡所能抱持友善的態度。而在台灣服務的宣教師從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以降,更是住在原住民村社當中。
相異點
1.荷蘭人最初前往兩地的目標截然不同。在新尼德蘭,荷蘭人主要目的是獨占與摩霍克人的毛皮交易,因此沒有披荊斬棘開墾農地,也沒有極力擴張治理領地,或是由母國引入大量人口。新阿姆斯特丹自始至終作為貿易口岸的角色沒有改變,印第安人也一直維持獨立主權,所以當新阿姆斯特丹長官威廉.基夫特(Willem Kieft)要求印第安人繳稅時,印第安人回應道,他們與荷蘭人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沒有必要遵照長官的吩咐繳稅。
然而,東印度公司治理台灣的目標是把台灣當成與中國、日本貿易的轉運中心。經過1636年麻豆社征伐之役及後來擴充領土的南北遠征後,荷蘭人進一步引進地方會議制度(Landdag),在地方設立官派長老治理,藉胡蘿蔔與棍子(Carrot and Stick,意「獎勵與懲罰」)間接治理全島。
2.儘管兩地教會都受阿姆斯特丹中會監督,宣教人員合作規模卻有極大差異。新尼德蘭的宣教師幾乎都是單打獨鬥,台灣的宣教師則都是以團隊形式宣教。
新尼德蘭從設立教會開始,從來沒有任何宣教師派駐在印第安人部落中,也因著缺乏接觸,米凱琉斯相當敵視印第安人的語言、文化和宗教。而派駐台灣的第一位宣教師甘治士,儘管對原住民文化和宗教也採負面看法,但他相信只要藉著治理及教育,就有能力改變原住民的文化和宗教。在這種信念下,甘治士住在原住民部落,學習他們的語言、宗教與文化。同時駐台灣的荷蘭長官也定期拜訪原住民部落,以建立雙方良好的關係。
3.政治現實對兩地宣教工作皆有很大影響,神學因素影響卻有不同。台灣的宣教工作,神學因素不容忽視,甚至曾引起論爭。反觀新尼德蘭,比較少看到神學影響的跡象。
4.兩地治理當局遭外力驅逐後,影響力存續情況不同。由於英國長官採宗教寬容政策,新尼德蘭的荷蘭改革宗教會仍保留教會財產和崇拜。占領台灣的鄭成功則禁止基督徒集會,所有宣教師不是殉教,便是搭荷蘭船隻離開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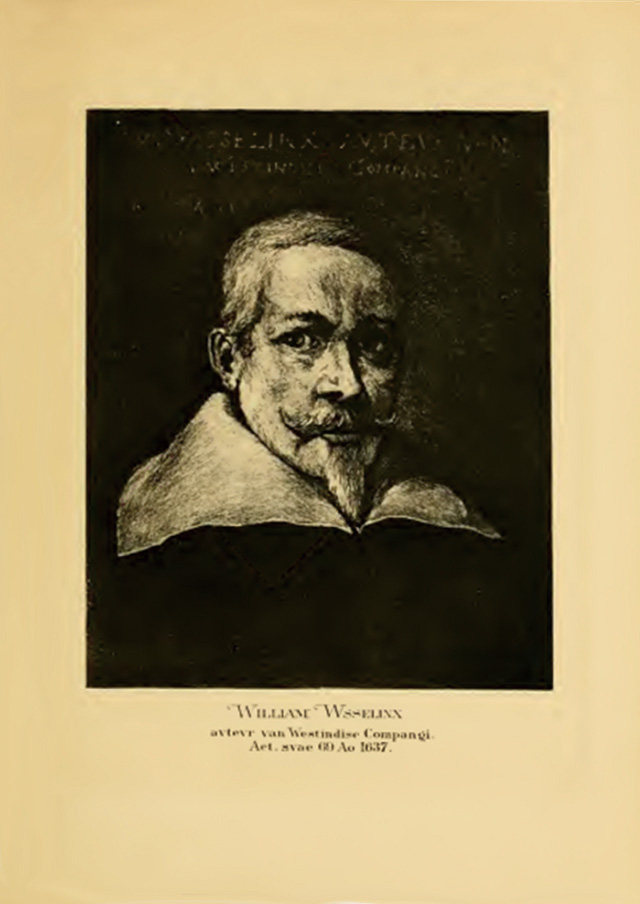
新阿姆斯特丹為何失敗?
以前沒有任何一本著作或論文比較17世紀的新尼德蘭與台灣歷史,但有論文比較新阿姆斯特丹與波士頓。耶魯大學教授馬克.彼得生(Mark Peterson)曾在其論文中指出,由於新阿姆斯特丹與波士頓兩地殖民者對城市定位不同,造成兩城市發展出現巨大差異。新阿姆斯特丹的定位為:
一個貿易的前哨站,裡面住滿士兵及野心勃勃的貿易商,他們知道如何在這個異邦榨取資源,以供應歐洲大城市消費,或是再出口。
在充滿商業考量的高度利用下,經過一段時間後,已出現破敗景象:
新阿姆斯特丹仍然是一個低度發展、窮困的地區,社會不靖;一塊醜陋、難以治理、瀕臨崩潰邊緣的殖民地。
在此同時,波士頓一開始的定位就是拓墾的殖民地,在英國受到壓迫的清教徒於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e)領導下來到此地,他們相信波士頓會成為聖經裡所說的「山上的城」(馬太福音5章14節),因而締造基督徒信仰典範及拓墾者學習榜樣。大量移民湧入波士頓,不僅帶來人力資源,也帶來大量經費,成為推動城市發展的力量。1630年英國內戰期間,移入波士頓資源大量減少,影響該地發展相當一段時間,新英格蘭經濟受到極大虧損,但是拜1640年代南美洲「巴貝多蔗糖貿易潮」(Barbados Sugar Boom)所賜,波士頓商人野心勃勃投入南美洲蔗糖貿易,然後發展成北美洲、南美洲與歐洲的三角貿易,創造波士頓全新且永續發展的基礎,因而由原先蕭條的經濟中復甦,並開始在新英格蘭地區扮演文化、政治及經濟的領導角色。

貿易派與殖民派之爭
馬克.彼得生的論文提出一個研究西印度公司的荷蘭學者也會提出的問題。雅普.雅各(Jaap Jacobs)在《新尼德蘭:17世紀美洲的一個荷蘭殖民地》(New Netherland: A Dutch Colony in Seventeenth-Century America)中指出,西印度公司商部之間針對新尼德蘭的定位與發展有兩派勢力互相競逐,一是「貿易派」(Trade Faction),一是「殖民派」(Colonization Faction)。貿易派認為新尼德蘭最主要功能是發展毛皮貿易,當時荷蘭在南美洲已經由葡萄牙手中搶奪部分土地,那裡原本就有蔗糖,不需要在北美洲另建立一個農業殖民地,只需建立一個能夠保護荷蘭人經濟利益的根據地。
殖民派則認為,在北美洲發展殖民地,除了可提供母國豐富的原料,殖民地也可以成為荷蘭母國產品的消費市場,只要在新尼德蘭限制發展任何手工業與紡織即可。殖民派成員有鑽石商奇立安.范.蘭瑟拉(Kiliaen van Rensselaer)、山姆爾.厚丹(Samuel Gordijn)等人。一般來說,貿易派較占上風,但是1640年代殖民派總算影響了西印度公司的決策,在哈德遜河上游原本以貿易為主要功能的奧倫支堡(Fort Orange)建立以土地擁有者蘭瑟拉命名的農業拓墾區「蘭瑟拉衛殖民地」(Rensselaer wijk Patroon),因此在新尼德蘭有貿易派主導的新阿姆斯特丹,也有殖民派經營的蘭瑟拉衛。雖然兩者定位不同,但畢竟有地理之便,農業殖民是否能夠插足毛皮買賣,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議題。

兩派之爭影響宣教
對宣教工作來講,重貿易或重殖民會影響他們對原住民的態度。貿易派將原住民看成原物料的供應者及貨品的消費者,雙方關係建立在生意往來上,因此擬定政策時會著眼於如何獲取更大經濟利益,避免任何危害貿易關係的作為,以確保雙方穩定的關係,所以一般來講,主事者不鼓勵帶有侵略色彩的宣教活動。這種態度和做法,台灣和新尼德蘭差異不大,但教會往往會抱怨,這種抱怨的聲音可同時在兩地教會的報告書中看到。
至於殖民派對原住民的態度,則受兩個因素影響。首先,殖民派多是1585年來自荷蘭安特衛普的宗教難民,對宣教一開始就非常熱中;再者,農業殖民與原住民生活地域免不了要互動,如果擁有相近價值觀,教會或宣教者能居間協調,可以減少許多摩擦和衝突,因此農業移民的主事者會鼓勵宣教。
另一篇相關的研究論文是討論荷蘭人「強制樂捐」(Brandschattingen)的問題,作者追溯荷蘭人1643年屠殺印第安人部落進而引發雙方戰爭的最主要原因,是威廉.基夫特強制要求印第安人樂捐。這是16世紀西班牙治理荷蘭時期最惡名昭彰的制度,威廉.基夫特也拿來用在新尼德蘭。簡單來講,強制樂捐就是「把錢拿出來,否則就把你全部的家畜抓走,放火將你的房子和田地燒成灰燼」。
根據與威廉.基夫特同時期的荷蘭人所寫的報告,可以看到他的詭詐:
他(長官)允許商人私自賣火器給摩霍克放及莫西干族,這兩族都是新阿姆斯特丹附近部落的敵人。但拒絕賣武器給阿姆斯特丹鄰近的部落,藉此向他們強索保護費。
這篇論文說明威廉.基夫特對印第安人發起戰爭,如何引發荷蘭母國另一場口舌之爭,以及對印第安人發動戰爭的道德問題。該文也提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他認為荷蘭人在新尼德蘭對印第安人宣教失敗,毫無疑問地有相當程度受到這次戰爭的影響。戰爭爆發後,雙方原來脆弱的信任自然蕩然無存,在互相敵視的環境之下,宣教工作無由推展,當然不會有任何宣教成果。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