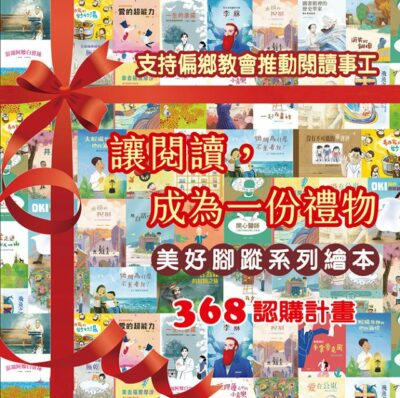◎陳嘉式
想不到馬偕的這一句話「寧願燒盡,不願朽壞」那麼被關心,不過在此想重提的是,馬偕所引用的典故中(參《台灣教會公報》3091期),最重要的是第三棵樹所表明的來日意願,它為了要「照亮別人」所以寧願成為火炬而被燒盡。它所不願「朽壞」的是,不願像第一棵樹所想要的,作偉人的棺材;以及第二棵樹所想當的,作大房子的建材。因此,每當提起馬偕所引用的這句話時,應當把重點放在如何當一把火炬,燒盡自己「照亮別人」,而不是他所不願意的朽壞或銹壞。千萬不要把如何朽壞或銹壞當作是宣教師的精神。
說到翻譯,到底要按字典而字譯,或按文化處境而意譯?中文的「我們」只有一個指謂而已,但台語的「我們」範圍較廣,可分為將對方包括在內的咱(inclusive);不將對方包括在內的阮(exclusine)。中文的「癢」也只有一個意思而已,但台語可分為皮膚的不舒服,例如因癬疥而chi?n;以及因搔撫使人發笑的ngiau。因為中文沒有咱和阮,以及chi?n和ngiau的差別,遇到這種情形,要將中文的「我們」或「癢」譯成合乎台語的正確意涵,一定要追查說話者或用字者的原本用意。他所說的到底是有將聽者包括在內的咱;或將聽者排除在外的阮?是因癬疥而起的chi?n?或因搔撫而來的ngiau?將台語譯成中文也一樣,那當中的不同點要多加說明。
Rust按字面大都指金屬的「銹」,偶而可指草木的「朽」。但因為它出現在有押韻的句子裡,當我們要把它譯入我們的文化時,我們要考慮的是它在詩句背後的意思所指的是什麼?那合乎我們文化的用字應該選哪一個?按其典故的用意木「朽」?或按字面的用字而木銹?無論是滬尾館中的或台神馬偕塑像的「銹壞」,都是先人在不知其典故下按字面譯成的。後人因為有機會得宣教師晏寶理(Bernard L. M. Embree)的說明而把它改正過來,這不但是我們求真的精神,也是使命。
(作者為前台神院長,退休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