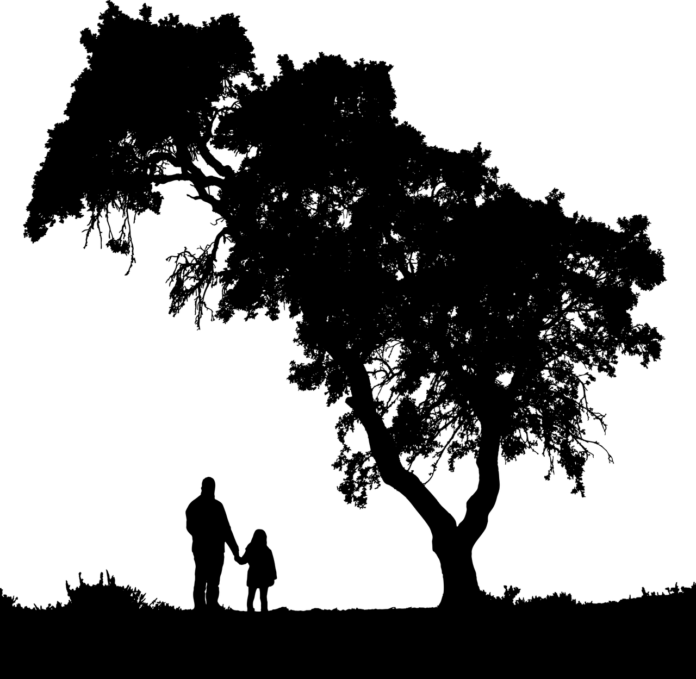◎劉曼肅
父親在我小時候就老了,我所認識的父親從未年輕過,他是那個十年生死兩茫茫、千里有家歸不得的流離者,即使家是那樣溫暖。
巧手做工
家是溫暖的。父親有一雙巧手,他親手做的木桌,是卡榫接的,不用一根釘子。家裡有很多巧妙的掛勾,有精準的線條,都是爸爸的傑作,在那日式的小木屋裡,到處都是爸爸的手藝。我每天上學前梳辮子,是在一個吻合在細長的木柱上、長方形的鏡子前,那是爸爸做的;木柱旁邊的棉被櫃,細心地用甘蔗板分隔,那是爸爸做的,我常常爬進去躲起來,也常常在那裡面尋寶。
我們家還有一塊擀麵板,起初是木頭,後來用鐵皮包起來,拿出那面板子,就表示要和麵、擀餃子皮、包水餃了,那是爸爸、媽媽合作出來的一餐。記得有一次,我和弟弟停不下來地一直吃,爸媽也不阻止我們,碩大的水餃,我們邊吃邊數,吃了二十幾個,因為實在太好吃了!那天我和弟弟吃撐了,只能大字形仰躺在地板上滿足地微笑。
揮灑書畫
爸爸的朋友都是喜好書法、篆刻的,他最擅長的則是水墨畫。我小時候學寫書法,是爸爸教的;學認草字,是爸爸教的;我很早就學會爸爸的簡體字。爸爸教我看書法的力道,要力透紙背,揮灑時仍要力量貫注;還教我用毛筆的濃淡墨色畫小雞和菊花,我覺得畫畫比書法有趣多了。我至今喜愛看文人畫,大約是有些東西深入了骨髓,為我的人生定了調。
我的書桌前掛的一幅字,寫的是「大江東去浪淘盡……」我總是邊寫作業、邊看字,不知不覺整篇背下來。家裡有很多父親的對聯和父執輩的字畫,我以為這篇是某位伯伯的文章,不懂也不覺得好,從沒想過是千古名文。讀大學的時候上到宋詞,老師指定要背這篇,我很得意,我已經會背了。但是直到我開始背誦,才知道我不會斷句,我只會整篇一口氣地背下來,用父親的鄉音,連錯字都背下來了,那時真笑壞了同學!
爸爸另一個給我深刻的影響,是在大藤椅上,我立於他背後,他一字一句地修改我的作文。直至我現在教小朋友寫作時,和他們討論的方式,都有爸爸的影子。我知道怎樣說孩子會懂,我知道接受指導,孩子會有什麼感受,因為這些經歷深入我的骨髓。
思索情理
考大學之前選填志願,我是自己填的,放榜之後,爸爸若有所失地問我,怎麼沒有填法律系?「法律系?那是丁組欸,我只愛乙組的科目!」爸爸沒說什麼。直到爸爸80多歲時枯瘦臥於病榻,媽媽跟我提起此事,說爸爸本來期待我當律師。我很震驚,我怎麼會是律師的料?媽媽說,爸爸常常覺得我能言善道,適合當律師。
難怪小時候爸爸常常跟我說一些法律的判例,跟我討論事情如何解析。例如,如果政府規定不能藏米糧,但他藏了,爸爸問我,我會不會去檢舉爸爸?我腦子裡只有正義,我說會,爸爸犯錯,不應該。爸爸很失望,他說:「妳這孩子,爸爸藏米一定是快要饑荒了,大家都要餓死了,爸爸的米一定也會給妳吃,法之外還有情、理啊!」我好羞愧,但我也好生氣,爸爸為什麼要這樣考驗我?
他徹頭徹尾是個文人,即使他以為在談法律,對我而言都是文學,我靠這些文化養分長大的!
包容安慰
爸爸跟我說很多事。
我初經來了,濕濕黏黏,那時衛生棉實在太貴了,只能用厚厚一疊衛生紙墊著,這讓我難以移動下肢,加上莫名地肚子悶痛,褲子一下就弄髒了,換了又換。我忍不住發脾氣了。這事很新鮮,因為我自幼是個悶葫蘆,沒發過脾氣。我鼓著嘴,我非常用力地對天、對地、對自己抵抗這身體上的不舒適,更何況這不是只來一次,它會定時來報到。我生氣為何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這件事?我生氣為何我不能避免這酷刑?
爸爸說,我們出去走走,我不要,爸爸說還是走吧!爸爸用腳踏車載著我,那時我已經長大了,有些分量,爸爸用力踩著踏板,我抓著爸爸的褲腰帶,聽見他喘息。然後爸爸說:「有些事,妳要學會。媽媽每個月來的時候都發脾氣,我都讓著她,過了就好了。但是妳可以不一樣,妳可以學會忍耐,讓不舒服過去。」
腳踏車來到順暢的一段路,風從身邊滑過,不管接下來是要往哪裡去,我的情緒都已經從沸騰的溫度冷卻,已是一片習習涼風,我不再抗爭。我一口氣吞下此生即將開始的每個月的咒詛,果真,我持續長年的經痛,都不曾再喊過苦、發過脾氣。原來,媽媽沒來由的脾氣有時候是這樣的原因,原來,婚姻中的不和諧,爸爸心裡有過這樣的孤單承受,我絕不要像那樣無理性地亂發脾氣了。只一句「妳不要像媽媽一樣」,就足以使我輕易地跨過了情緒的門檻。
傷心公案
我終究還是傷了爸爸的心,但這一件公案我至今想不透。
那時我獨自到台北讀高中,我不適應台北,我很孤單,在《野鴿子的黃昏》、《泰戈爾詩集》、心理學、憂鬱症、耶穌的比喻……永遠搞不定的數學、英文……中打轉。爸爸唯一一次到了我租屋的地方,在長安東路的公寓,我恰好不在,室友事後告訴我,父親來過了。她吞吞吐吐地說,父親跟她說了一些奇怪的話,看起來好像哭過。我不相信。
後來,我質問爸爸,為何到台北不先跟我說一聲?神出鬼沒地來了又走?爸爸反倒質問我,為何在紙上寫「我恨爸爸」?
驚愕中,我一直回想自己為何寫「我恨爸爸」?我有這麼恨爸爸嗎?我說,我寫的是「爸爸,我恨」,可不可以不要隨便看一張計算紙上的塗鴉來定我的罪?
我百口莫辯,因為爸爸相信我恨過他。那時期,我們經常為一些觀點辯論,我們辯論關於儒家與聖經的比較,關於獨一真神與中華文化的相容問題。我們也辯論過,是否有「代溝」?明明就存在,何需辯論?但我不知這是爸爸的底線,他傷心了。
難報親恩
父親88歲時纏綿病榻,我終日守在醫院,看著爸爸辛苦地與病魔搏鬥,他離去日無多,我想起還有一件無頭公案,想要為自己平反,當我提及此事,爸爸卻阻止我說下去,他似乎已有定見,不需要我多言。我很委屈,我是被冤枉的,那張紙上我到底寫了些什麼?我恨自己竟然毫無印象!
爸爸與我之間,些微的信任的裂痕,就是這樣發生了,是否戰爭和離亂的恐懼,使他的心靈有隱密的傷痕,是我不懂也不能參與的?爸爸的羽翼已經不能遮蔽我,我必須衝出去尋找自己的天空。我有時候感覺到爸爸老家裡,我那曾祖母壓在箱底的前清朝服,那鳳冠霞帔,是一種揮之不去的遺毒。
即使如此,我漸漸發覺,那些黏在我身上的父親的影響,是我生命裡的基因,我越來越像父親。我自憐的情緒像父親,我鍾情於庭園植栽像父親,我喜歡望著水墨畫發呆像父親,我用鉗子製作鐵絲勾像父親。
我在一個溫暖的家成長,爸爸隻身來台,卻為我和媽媽、弟弟撐起了一個溫馨、舒適又穩定的家,他吞下了所有的眼淚、悲哀,完成了白手起家這困難艱巨的任務,這恩情我是無以回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