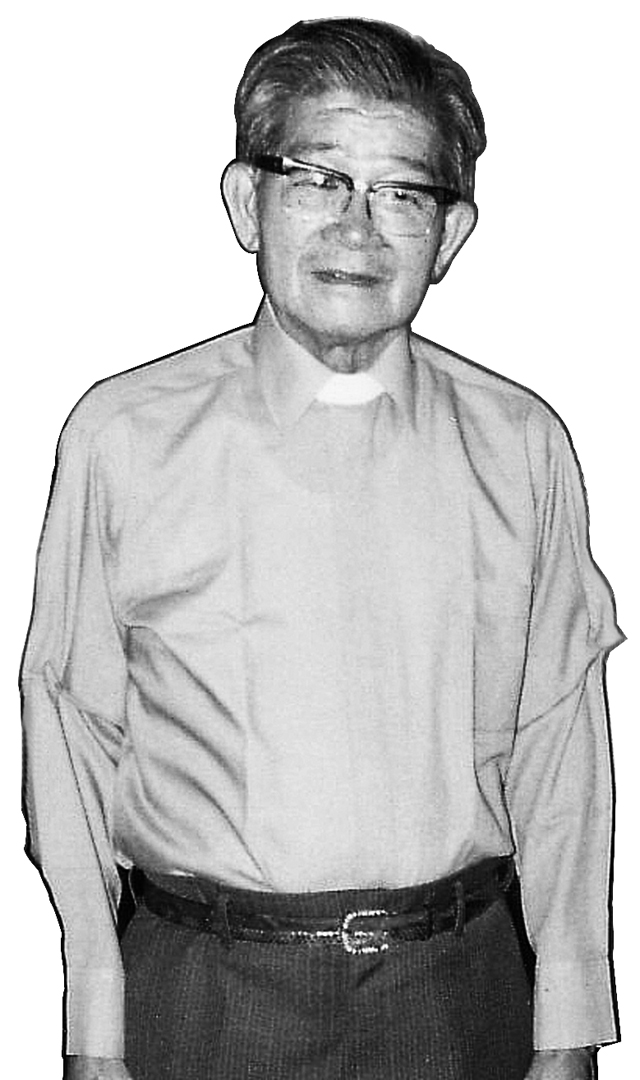本文摘譯自1970年10月6日,黃彰輝於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演說。
原文/黃彰輝 摘譯/阿骨力
我之前嘗試從文本(text)和處境(context)的相互作用來看待使命(the mission)與教會宣教事工(the missions),並使用我個人經歷去描述它。當上帝的文本(text)和處境(context)之間進行的互動成為我個人存在的經歷時,就產生種種議題:一部分是自我認同(self-identity),另一部分是自我決定(self-identification)。這引起更進一步的問題,一方面是忠實於自我,另一方面是形成自我。這兩個是形影不離的;它們必須分辨,但又不可分割。當我拿著我的日本護照,我必須住在日本的處境下。但問題是,我如何在處境中達成自我認同──因為上主把我放在那裡──能在此時或隨時,去發現並維持我自己的自我認同?
伴隨這個觀點,我回到現代宣教及它們的成就──在亞洲及全世界創造年輕教會,並在教育、醫療及其他可見或不可見的領域中,形成龐大的宣教事工。然而,我知道,當代宣教之所以被嚴厲攻擊及批評,可能是因為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時代結束的時刻。前一個世代或許被歸類為殖民時代,而現在進入眾國紛紛獨立並建造新國家的時代。在轉型時,宣教事工當然比以前令人質疑。所以我們必須提出這個問題:「以耶穌基督之名的自我決定──祂的宣教──能保有多少對於上主而非對自己委身的真實?」當宣教事工被抨擊且遭受內部及外部批評時,我們不應該害怕。
跨越邊境的神學意義
教會的全部使命經常涉及自我批判的雙重程序。我稱一種為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另一種為處境批判(contextual criticism)。在這裡,我想多談文本批判,我們必須仔細思考自決的問題,以及我們的時代是如何與宗派、殖民、敬虔有著高度關連。然而,我們也需要思考如何能再一次更潔淨、更忠實於文本或是文本所指出的。
宣教需要跨過邊境,但跨越邊境並不是宣教。在今日社會中,跨越邊境是常有的事。有些是為了娛樂,有時是為了商業;難民跨越邊界是為了逃離暴君,有些人跨越邊境則是為了國家利益、甚至為了戰爭及侵略。誠然,跨越邊境是宣教的整體成分,但跨越邊境並不是宣教本質,因為宣教事工涉及對其他生命或其他文化在信仰的翻譯,所以決定性的問題是:「什麼是跨越邊境的神學意義?」「為什麼這趟旅程是必要的?」
儘管宣教事工有困境及限制,更新及潔淨的基督教宣教事工會繼續在今日世界具有決定性角色。因為不論結果好壞,整個世界的救贖是不可分割的。在美國、亞洲或是在非洲所發生的,將為世界所知。更重要的是,在某處發生的事情會影響其他地方的上百萬人。到目前為止,這個世界第一次面臨一個事實:一同生活、一同毀滅,或一同被救贖,這個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宣教事工、跨越邊境在這個新的處境裡,再一次在今日世界扮演創造性的角色。
宣教事工是教會使命的試金石
使命(the mission)及宣教事工(the missions)的分別非常富有啟發性。但卻令我非常不安,當這些放入口號,「走出宣教,邁向使命」(missions out, mission in),彷彿它們是二分法的衝突。我不相信如此,然而,我們可以考慮用使命(mission)來看見宣教事工(missions)。它是我堅強的論點和堅信,宣教事工是教會所有使命的試金石。
用單數和抽象來討論所有的宣教(the mission)是好的,那樣的討論容易用普世性的智慧來說:「慈善自家中開始,也在家中結束,因為許多問題和事物需要在家完成。」然而,宣教事工(missions)在教會宣教(the mission)是決定性的測試。
單數式的宣教有著比較近代的起源。它大部分是因為現代宣教事工的成就,導致教會開始覺醒自己不再是慈善機構,而是運動、是使命。就像荷蘭改革宗神學家維瑟福(Willem Visser’t Hooft)說的,宣教事工是對信實與否的測試,也是對門徒的關鍵考驗,它是教會真正受試驗的地方。你是否被說服到一種程度,願意跨越邊境跟其他人宣講好消息?或者你認為,基督教只是眾多宗教中的一種,只是私人的考量,你抓住它只因碰巧住在某個特定地方?
我相信宣教事工在教會的使命中不只是決定性的測試,它也是信仰及門徒的決定性測試。在一方面,今日宣教事工的危機根源是更深的危機,是信仰的危機。我們不要試圖閃躲這個議題,即便我們被所有問題圍繞。這是為什麼偶然批評,會成為嚴肅事情。為什麼跨越邊境涉及如此多獻身的僕人、完成如此傑出成就,然而在這個決定性的點上卻有一些問題?
只在教會中的宣教事工看教會的使命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更深入,所有宣教事工的背後是上帝的使命(Missio Dei)、耶穌對所有人的使命。這帶我們回到所有文本所指向的,我們需要再一次問自己,確立我們的信心,並更新我們自己與這個事實的關係。
在乎眾人的獨一者
我是第三代基督徒,但我的確被某種事物抓住,某種聲音告訴我說,不會留下我單獨一人。我的祖父在他的處境中被它抓住,而有著在數年後信仰變成傳統的危險。為什麼這個聲音沒有離開我?我祖父曾是道士。他曾在世俗世界中表現良好,但在他心中,曾有某種事物不停止令他感到不舒服。我猜他曾不顧一切地吶喊:誰在乎我?在這樣的處境裡,他被浪子的比喻抓住;他曾說過,他發現了在乎他的獨一者(the One)。
在中國及東南亞有成千上萬人,但誰在乎在福爾摩沙的1400萬人?他們一度是日本的獎品,後來是蔣介石的獎品,接下來是毛澤東的獎品,但誰在乎?是的,不只亞洲的民眾,甚至幾千萬的人都在吶喊「誰在乎我?誰在乎我們?」正是那個聲音、那個不會留我獨自一人的聲音說:「我在乎,我甚至不吝惜我的兒子。」這就是宣教運動的開始。我無法證明,但正是這個聲音告訴我:「基督愛我,我知明,因為記載於聖經。」
宣教運動會被測試,是因為它會遇到獨一者,伴隨這個運動,把祂移向他人,在恩典中注入、在創造之始,甚至在這個敗壞世界裡,祂差遣祂的兒子。這個神聖運動把祂自己移出,這是祂在乎的表現。宣教運動是決定性的測試,因為它涉及自我向外移動,跨越邊境則成為神學及神聖的必須。
上主不只在乎教會及在其中的人,祂在乎這個世界,而宣教運動是朝向世界的。這個運動的方向及目的地是這個世界。是的,宗派的感染會讓我們在乎擴張自己的宗派,甚至讓我們忘記我們涉及在神聖的運動裡。如果我們被這個朝向世界──朝向這個拒絕祂同時又吶喊「誰在乎」的世界──的運動抓住,我們就會聆聽。
上帝的使命三要素
當我把教會的宣教運動及全部的使命,都放在上帝的使命的探照燈下,我發現三個重要因素:
第一,這趟旅行為何必要?動機是什麼?動機是不尋求自己的愛。生命的最終實況真的有一種愛不尋求自己嗎?真的有一個祂者(He)不尋求自己嗎?我時常談論改革宗傳統裡關於神的榮耀和主權,我發現要看見有一位神不在乎自己的主權、榮耀,甚至為了愛的動機而走出去,對改革宗傳統而言很具有挑戰性。祂並不尋求祂自己,為了教會更新及純淨宣教運動,宣教運動必須把人們帶到愛的探照燈下,而不是尋求自己。
今日有許多宣教士向外走出去,為什麼?什麼是你們的動機?有時我覺得,我這樣講聽來有點忘恩負義,但或許須減少宣教士的數量,因為他們應該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對你們,宣教士只是個職業,你們有時感到有趣,或只是好奇,或者你們跟祂一樣在乎?
第二,愛不只應該是使命和教會宣教運動的動機,終點也必須是愛,因為上帝正建立愛的新人類。
第三,不只動機及終點,手段也必須是愛。齊克果在《哲學片段》裡的話很有挑戰性,「然而,愛不只改變所愛的,也改變它自己。」這是道成肉身的奧祕,這是耶穌基督在世上服事的奧祕。這也是上帝的奧祕,上帝如此在乎、甚至不吝惜在十字架上拋棄祂的兒子。
我們總是記得我們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呼喊!人子並非來受人服事,反而是服事人,為多人捨己當作贖價。神聖運動從自我走出──從道成肉身到十字架──愛是動機,它的目標是愛,至於手段,也一樣是愛。或許,在殖民風氣鼎盛的時期,當代宣教運動沒有仔細思考最後一點──手段。亞洲神學家小山晃佑將他們的手段稱為「火藥及膏油間的對話」。當代宣教運動曾有豐富的膏油,但也曾有大量的火藥,文本批判要求我們回到上帝的宣教探照燈下,再度發現我們的自我認同。在宣教運動裡,我們必須認同今日受苦的世界,我們需要注意今日的亞洲處境,但我們也必須再次被更新、潔淨、成聖及原諒。我相信並禱告,宣教運動會從過去的偉大與軟弱中學習,再次更新及重生。我們可以像宣教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一樣,期待從神而來的大事並嘗試為祂做事。宣教運動是教會整體宣教的重要測試、也是信仰的重要測試。我們將被獨一者抓住,祂說我在乎、我給你們我的兒子,我需要你們在我家。
教會是/存在(is),因基督是/存在(is):教會在宣教運動(missions)中因基督在使命(mission)中。這個次序絕對不能更改。祂在使命(mission)中,因祂的父親派遣祂。在這個使命裡,我們都被抓住。我們都警覺我們只是土的器皿,我們的蒙召不多也不少,呈現出Mission Dei,是這位會在乎的上帝的使命。而且藉由上帝的恩典,我們的宣教運動會像祂的使命。
今日的亞洲處境仍然需要宣教運動,甚至比以前更需要。但是它們必須被上帝的使命潔淨與更新。如此一來,在一個令人興奮、涉及千百萬人福祉的建國處境中,我們可以一起走入新紀元,年輕的教會與年老的教會可以攜手共同服事這位在乎的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