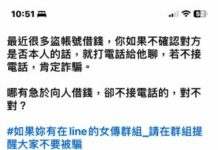◎金毓渝
大阪市櫻宮高中體罰自殺事件最近在日本教育界鬧得沸沸揚揚,曾帶領該校籃球隊數次進軍全國大賽的教練,以「激發隊員的士氣」「燃起鬥志」作為體罰理由,雖曾被投訴過,但因師生權力地位懸殊,大阪公益通報系統過水般地判定「不存在體罰事實」,最終導致無法挽回的悲劇。
這樣看來,問題不在體育是否與德育有關,而更多出在教育當局想藉由體育實施什麼樣的道德教育?日本「體育」教育,受到明治時代「富國強兵」政策影響,加上儒家「長幼尊卑」的禮教,一切「不合理」的要求都被「合理化」為鍛鍊堅忍不拔的性情。不單教育手段的暴力「偶爾」可因最終救贖目的而「加持」。猶有甚者,例外變成常規,救贖暴力(redemptive violence)被神話為一種必然,「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
體罰迷思堪稱與死刑不相上下,都體現了救贖暴力的思維。救贖的暴力,既有著拯救作為其目的,為何不能真正作為暴力的救贖(the redemption of violence),而淪為一種迷思?癥結點與救贖暴力的神話特質脫離不了關係,在都帕(Theodore L. Dorpat)《刑罰的罪行:美國的暴力文化》一書的解構下,救贖暴力的迷思有三項重要特色:1.常將暴力施用過度理想化,完全不考慮冤、錯、假的情況,及其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甚至兩極化,只有我們「正義之士」對付他們「邪魔歪道」。2.取消社會大眾對於罪犯成長背景所可能有的罪咎感及同情心,這種內在情感是採取暴力作為的最後內在防線。3.執政當局藉由操弄這類迷思,得以讓人們順應一個更大的結構性不義體制,於是成就了個人犯罪的溫床。
救贖的暴力往往成就尼采式「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宿命,它非但沒有打敗惡魔,反而「打出惡魔來」(beating the devil out of them)。研究指出,受到體罰的學童,道德人格較不健全,日後罹患憂鬱症及自殺的機率較高,職業生涯的成就較低,也較易犯下家暴、謀殺,及其他暴力侵害案件。美國數次針對獄囚的大規模統計結果,亦證實了上述的觀察,約有高達60~90%的獄囚,在孩童時期曾是暴力事件的受害人。
這些研究說明,為何死刑嚇阻效力的相關研究違反預期,非但不具嚇阻效果,反倒有殘生殘忍效應(brutal effect)。美國犯罪防治統計中,當某一州開始施行死刑後,犯罪率往往不降反升;廢止死刑的州,其襲警案件的機率比起保有死刑的州來得低,其囚犯及獄政人員遭到終身監禁者的暴力攻擊機率也較低。以救贖為名的暴力,終究會自陷在暴力的惡性循環中,這項鐵證應該促進基督教會在面對體罰及死刑的議題上,重新斟酌,如何從救贖暴力的迷思,邁向對一切暴力的終極救贖──和平非暴力。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