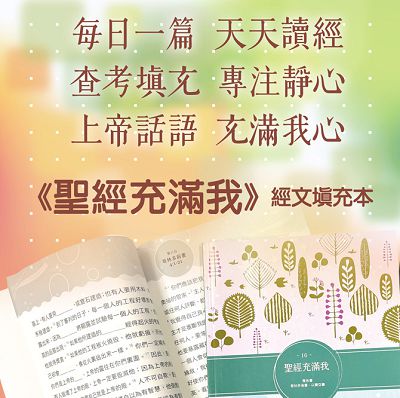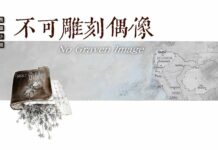從《迷離劫》看阿薩亞斯的女性觀點
小鏡頭大世界:心靈小憩站長陳韻琳將不定期撰寫系列文章,引領我們透過電影導演的鏡頭解讀世界,看他們如何以藝術手法呈現種族問題、女性主義、社會弱勢等議題,啟發我們關懷世界的另一種眼光。
台灣對法國導演奧力維耶‧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的認識,多是因為他曾經是影星張曼玉的老公。張曼玉跟阿薩亞斯是1996年在一起拍攝電影《迷離劫》(Irma Vep)時相愛並互許終生,張曼玉說自己當時對送到家裡的劇本沒有一個滿意,因為裡頭全是無聊重複的角色,她曾說:「如果後來奧力維耶沒有來敲我的門,我現在可能已經在做別的工作了。」他們有一段短暫的婚姻,但隨著張曼玉回香港拍片,兩人聚少離多,最終仳離。
多重角度模糊分際
阿薩亞斯跟張曼玉首次合作拍《迷離劫》,所採用的形式,深刻突顯了《迷離劫》意圖探討的主題。
首先,阿薩亞斯讓導演的鏡頭入鏡了,也就是說,這是一部拍攝「導演在拍電影」的電影。每逢導演的鏡頭入鏡,都會產生特別多元的詮釋性,因為那至少包含了觀眾的詮釋角度、真實世界導演的詮釋角度、電影中導演的詮釋角度,以及電影中導演拍出來的故事自身的角度。
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演員飾演的電影工作從業人員,跟導演不時摩擦、也彼此摩擦,讓觀眾不自覺地忘了真實世界中掌鏡的導演與鏡頭的存在,而將劇中的導演角色視為真正的導演。阿薩亞斯將電影中導演取名「雷奈」,卻將張曼玉飾演的女主角取名為「Maggie」,正是張曼玉的英文名,這些設計都增加了虛擬與真實之間分際的模糊,而這正是阿薩亞斯《迷離劫》高明之處。
正因這虛實分際的模糊,當我們看到電影中的導演談到自己對伊瑪(Irma,劇中劇的主角名)的慾望投射時,再對照真實世界裡阿薩亞斯跟張曼玉果真出現短暫婚姻,便似乎順理成章地讓「戲中戲」延伸到「戲外戲」,使八卦不真的只是八卦。單就《迷離劫》的電影形式,已可看出阿薩亞斯不同凡響的執導功力。
阿薩亞斯選用這樣的電影敘事形式,與他想透過《迷離劫》探討的主題有關,即:拍片導演如何透過鏡頭解讀戲外演員、戲內角色,往往會被自己的慾望牽引、誤導,最終是「錯的真美麗」。
虛實角色認知錯亂
電影中的導演雷奈要重拍一部經典電影。這經典電影確實存在,是法國導演Louis Feuillade於1915年拍攝的《Les Vampires》,這部連續10集的默片,是早期的犯罪經典名片。
重拍經典永遠是天大的難題,因為後人不只要擺脫經典留下來的刻板印象,還要按自己的時代重新解讀、詮釋。導演雷奈的難題,則是如何詮釋身處一大群壞蛋男人中的壞蛋女人──蝙蝠黨的皇后伊瑪,她著緊貼全身的皮衣,是蝙蝠黨的靈魂,也是引發男人慾望炙手可熱的人物。
電影中,雷奈某次在摩洛哥看到Maggie主演的港片《東方三俠》(正是真實世界中張曼玉主演的電影),電影中的異國情調觸發他的靈感,興起讓Maggie飾演伊瑪的念頭。此時的雷奈在電影界已經沒落,因此他的壞脾氣讓工作人員更加無法忍受,工作人員之間也時有摩擦,所以Maggie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法國,不久後就陷入背後論長道短的口舌是非中,處於一個不算愉快的工作環境。
但是讓Maggie處境更艱難的,是當雷奈真正跟Maggie近距離一起工作後,他無法再從Maggie身上找到靈感,因為雷奈現在認識的Maggie,並不是《東方三俠》中的Maggie。隨著拍片過程波折不斷,雷奈的脾氣也就越來越不好,越來越惹人厭,這當然不是Maggie的錯,可是卻是因Maggie而起。
在一次失敗的拍攝與剪接之後,雷奈忍不住找Maggie私下晤談。雷奈說:「我是在生自己的氣,因為我看到的是沒有靈魂的影像&hellip&hellip我的意念來自你,穿上戲服的你,結果是幻覺。我以為我進入了事物的核心,結果是幻覺。」
Maggie卻無法理解何以雷奈將伊瑪這個角色看得如此沈重,她說:「伊瑪只是一個角色,一個遊戲。」Maggie站在她女性的立場討論伊瑪:「伊瑪很強,沒有她就沒有蝙蝠黨。」
但雷奈無法抽離Maggie來看伊瑪這個角色,他仍舊在兩者之間混淆,他說:「我對妳有興趣,伊瑪只是我慾望的投射,但這樣下去,妳會無戲可演。」
雷奈曾經想詮釋的伊瑪是「賦予壞蛋蝙蝠黨靈感的女神,最後卻成為敵對勢力的籠中鳥」,如今拍片走樣、失敗收場,他卻改了詮釋:「她看哪個男人強,就跟哪個男人上床。」
Maggie說:「ok,她沒道德觀念。但這有問題嗎?」
這段談話不僅反映出雷奈將Maggie與伊瑪重疊形象而產生的錯亂與不知所措,也反映了雷奈「投射慾望」的結果。他對伊瑪總是愛上強者而移情別戀無法接受,因為他自己是一個沒落、過氣的失敗者,他知道無論伊瑪或Maggie都不會選擇他。
跟雷奈談過話之後,基於專業演員的自我要求,Maggie回到旅館後,嘗試讓自己徹底化做伊瑪,她穿著戲服,按著劇情內容,在旅館偷偷地上下樓梯,還偷窺一個房門未上鎖、在房內裸體跟情人打電話的女人,再偷了她的項鍊&hellip&hellip。Maggie讓自己去感受著性格深處可能分裂出來的伊瑪,企圖讓伊瑪不再「只是一個角色」。而這個從Maggie自我分裂出來的伊瑪,也成為她自身慾望的延伸,是女性自主情慾的詮釋。 
雷奈大勢已去,他最終因酗酒而住進療養院,舊經典新詮釋的工作旁落另一個導演。新導演上任第一件要做的事卻是撤換女主角,他說伊瑪徹徹底底應當是法國人,跟華人何干?不僅如此,他強調伊瑪勢必是出身中下階層藍領階級的流氓。然後他講到自己的困境:「已經很久沒有收入,一直在領救濟金過日子。」原來他現今正是屬於中下階層,而伊瑪這個角色轉而成為新導演的慾望投射。
隨時代變遷的慾望投射
阿薩亞斯將《迷離劫》片名取名為「Irma Vep」其實有很深的涵義,因為它正是電影中經典老片《Les Vampires》各個字母的倒錯、拼湊,隱喻劇中導演雷奈最後像酒鬼胡鬧般,將原本的經典電影搞得一團混亂。到最後,Maggie演不了伊瑪,雷奈也不復是過去的自己,他在潦倒中失去了自我,而新接手的導演在解釋伊瑪這個角色時,也立刻投射自身落魄的處境。
雷奈與新導演的共通點在於,他們跟1915年導演Louis Feuillade同樣從男性的眼光來看待伊瑪這個角色,伊瑪的詮釋表現出男性慾望的投射。但他們無法想像的是,他們如今與Maggie置身在20世紀末,是一個主張女性性自主、多元情慾的時代。因而離開鏡頭的生活中,一個處理戲服的工作人員,也是女同志,看到身著皮衣的Maggie時,也對她產生慾望,如兩個男性導演一般視Maggie為尤物,她也愛上了Maggie。但他們都沒有發現的是,Maggie自我分裂生出伊瑪時,並不是被動地反映男人、女人慾望的客體,而是不受制於他人的主體。
因此,對照1915到1996年,伊瑪從一個慾望投射的客體,轉變成情慾自主的主體,反映出近100年來男性掌控女性,到女性自主多元情慾的時代變遷。這正是真實世界中掌鏡的導演阿薩亞斯,透過伊瑪要訴說的內容。
戲外戲走出迷離
如同一開始說的,因為形式的特別,這部電影呈現了觀眾的詮釋角度、真實世界中導演的詮釋角度、電影敘事中導演的詮釋角度以及電影中導演拍出來的故事自身的角度。也就是說,阿薩亞斯在電影形式中已經預設了我們觀眾的詮釋角度。偏偏阿薩亞斯愛上了飾演Maggie的張曼玉,上演了一場戲外戲。所以我們該怎麼看待伊瑪?又似乎多了戲內、戲外的解讀。
張曼玉回憶拍攝《迷離劫》那段時間,說:「有人跑來跟妳說,到巴黎6個禮拜吧,妳會和一批完全不認識妳的人一起工作。那種感覺真的很舒服,他們真的是一批熱愛電影的專業人士,我拍《迷離劫》拍得非常愉快。」後來她跟阿薩亞斯仳離,是在拍王家衛的《花樣年華》之際,因為拍片過程比預期久,導致夫婦倆聚少離多。還記得《花樣年華》中張曼玉的抑鬱惆悵嗎?她說:「12個月過去了,電影卻沒個影兒。我們每天都在拍,但是王家衛只是在旁邊觀察,他的腦中根本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故事。你一定要回到同樣的場景、講同樣的台詞6遍以上,它才會變成銀幕裡的東西。」
阿薩亞斯與張曼玉離婚後,於2004年再度跟張曼玉合作,拍了《錯的多美麗》(Clean),張曼玉因此片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女主角獎。阿薩亞斯跟張曼玉在一起的時候,就一直想為她量身打造一部專屬於她的片子,只是沒想到直到倆人離婚後才完成這個願望。他自己認為,這時候的他對張曼玉私密的個性有十分的了解,所以他將張曼玉從沒有在電影中出現過的一面表現出來。
回想《迷離劫》中的台詞:「我的意念來自妳,穿上戲服的你,結果是幻覺。我以為我進入了事物的核心,結果是幻覺。」從戲外戲的角度來詮釋這段話,結果阿薩亞斯是透過短暫的婚姻,看見了張曼玉不為人知、私密卻真實的面貌,結果造就張曼玉事業的另一次高峰。 
.jpg)
 
 
 
 
 
 
 
 
 
 
 
 
 
奧利維耶‧阿薩亞斯
(Olivier Assayas)
1955年出生於法國,父親亦為導演,從小耳濡目染,早期工作即協助父親拍攝電影。1993年金馬影展曾為他辦導演專題,此後與港台產生淵源。一般咸認1996年與港星張曼玉合作的《迷離劫》是他最成功的作品,1997年曾為侯孝賢拍攝紀錄片《侯孝賢畫像》。他是90年代崛起的新一代導演,被法國影壇視為新浪潮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