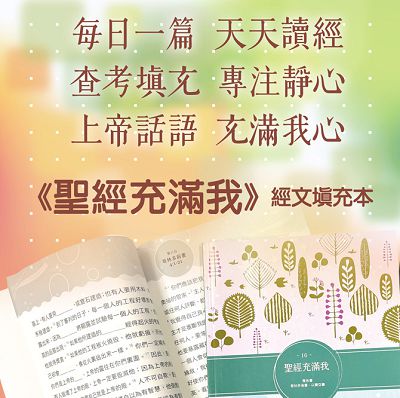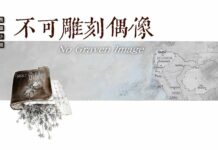◎吳易叡
記得5年前,從朋友那裡接過Todd Gitlin的小書《給青年行動者的信》。當時只不過和朋友們合製了一張專輯,作品旋即負載了革命的符號。決定遠行的時候,只問自己能夠學些什麼,不問學術能夠做什麼。那時,只問自己能不能真的思索出什麼東西,而不要當知識的弄臣。而今茅塞依然未開,許多才剛相信、才逐漸洞悉的符碼,在極端異化、質化的世界裡早已褪盡光芒。
一般人很難把「革命」和牛津如此食古的刻板印象連結起來,一面深入經院,一面撐船,那些不安於室的臉一一逐漸映在水面。13世紀的羅傑‧培根在愚人橋畔思索,反對典籍的爭論,提倡經驗的重要。17世紀約翰.威爾金斯和其他的自然哲學家在瓦旦學院的草坪上,倡議基於假設、驗證和團隊合作的知識生產方式,才有今日被廣納的科學方法。
信仰也是如此,19世紀的牛津運動中,揭竿者反對教會偏向羅馬,力圖發展宗教社團生活,基督徒在社會生活中的責任、對於社會問題的重視才再度獲得強調。而被後人追念的,卻也不見得是虔誠的信者。19歲浪漫詩人雪萊因為散發《無神論的必然》被大學驅逐,他的一生顛沛流離,最後在義大利死於船難,但是雪萊的衣冠卻被帶回了大學學院,以大理石鑿刻的蒼白裸身供人憑弔,大學也把陸續購得的雪萊書信當成重要資產。
我的資格考考官是科學史的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1960年代他寫的博士論文是牛津運動首腦Pusey的哲學思想,畢業之後才開始專攻科學史,研究伽利略和羅馬教會的關係。擁有大教授的頭銜,想必非常「牛津」,孰料在他寫論文的階段,竟也全程參與了1968年學運,在反道德封建和追尋自由的浪潮裡,學生佔據並廢止了大學法庭;大教授在論文答辯時拒穿學袍。
而多數人對於中古大學仍然維持著一股天真的想像,1930年代,徐志摩遊學劍橋,想拜哲學大師伯特蘭羅素為師不成,寫下了名作〈再別康橋〉,他的耽溺讓大學城蒙上一層浪漫的雲彩,但他所不知道的是羅素因為反戰立場,被三一學院罰款並革職。浪漫的文采並無法呈現懷疑論者的咄咄,羅素說:「在我的旅程中,一切值得學習的,並且在劍橋習得的事物,逐漸破碎&hellip&hellip。」
古城的夏天,經常可以側耳聽見來自台灣的童言童語。回頭一瞥,大群的孩子穿戴著名英文補習班的T-shirt、帽子和背包,在商業公關的包裝之下,大學城依然倨傲著她悠久的歷史,依然享受著哈利波特替基督聖堂賺的滾滾財源,依然鋪著文青筆下那「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學院裡的高桌晚餐依然奢華、偏執、無視,卻成為記憶裡如同馬克思語:「一切堅固之物都已煙消雲散。」而我已經悄然離開,不帶一絲浪漫想像,下一個目的地尚未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