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慈美(生態關懷者協會創會理事長)
疫情爆發不久的2020年,日常中有個令我震撼的經驗:一歲半的小外孫坐在娃娃車上進入大賣場時,居然主動伸出雙手,要讓入口處服務的阿姨在手上噴酒精!我沒有為外孫的靈巧高興,反而為他小小年紀就學到這種反應而心疼、感慨。現在的小孩,長大之後,究竟要面對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隨後,有「環境倫理學之父」之稱的羅斯頓牧師(Holmes Rolston, III)寄來一篇訪談文章(註1)給我。再過兩年,也就是台灣疫情開始有較大變化的2022年春天,我又收到已經高齡90多歲的羅斯頓牧師寄來一篇長達20頁的論文(註2)。我把這兩篇文章全文翻譯之後,濃縮成一篇在復活節分享的信息〈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
我們為什麼關心後世的命運?
2022年4月下旬,台灣新冠病毒的確診人數開始大幅上升的時候,我正好在聯經出版社看到2月出版的《未來關我什麼事?》(註3),立刻買回來拜讀。
譯者在導讀中指出:「偤太裔出身的薛富勒教授十分關注社群傳統與道德之間千絲萬縷的緊密連結,更擅長就近取譬,以生動活潑的思想實驗直指人人心中的保守面向,在崇尚功利、講求效益、只問結果、不擇手段的這個時代裡,點出真正深植人心的永恆渴求。」(頁004)「若是大家都看了這本書,都願意多想想我們有什麼樣的理由替後代操心,是不是就更能好好對待我們眼前的世界,能更好好處理手上的事務呢?」(頁010)
封底最上面一段文字指出:「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可能會使後代的生活變得更糟,但究竟為什麼要關心那些在我們離開很久之後才出生的人命運如何?」
接下來,同樣在封底,有下面三段文字,簡單介紹全書特色:
● 非關道德 一些哲學家將「為什麼要擔心下一代?」的疑問視為道德責任的範疇,並認為我們有出於慈善考量的義務來促進後代的福祉。不過,薛富勒考慮了更廣泛的層面,即後代對我們的重要性。儘管我們對於人類延續性的價值缺乏一套成熟的觀念,但我們對後代命運投入的程度,比自己所意識到的要來得多。我們現有的價值觀中隱含著各種強有力的理由,希望世代的聯結在有利於人類繁榮的條件下延續到無限的未來。
● 因為愛,所以重視 這意謂著,我們關心人類未來最強有力的理由,取決於我們現有的依戀與保守觀念,以及維持自己所珍視的事物的傾向,而不取決於單純良善或道德義務。後代與我們這一代間存在著一種互惠關係,能為我們此刻的許多行動賦與意義;而我們此刻的許多行動也能確保後代生存的可能性,或是擁有更好的生存環境。
● 回歸自我 薛富勒的觀點不是要求我們去發揚或抑制對後代的關注,而是藉由思辨「為什麼要擔心下一代?」這個問題的本質,了解自己如何思考生活中的時間維度與價值認知;對於諸如氣候變遷、環境保護等跨世代的議題,也能提供另一種切入與判斷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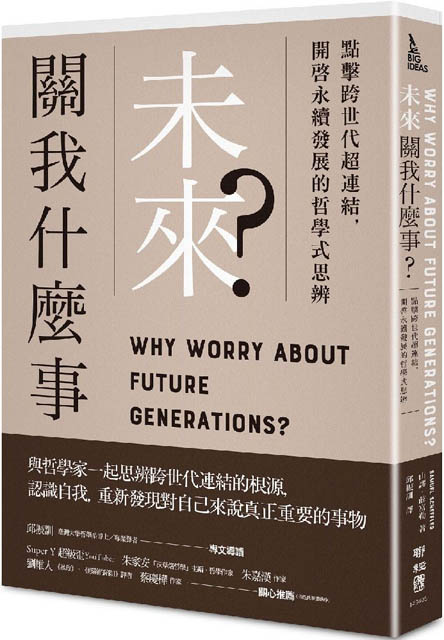 《未來關我什麼事?》各章心得
《未來關我什麼事?》各章心得
1.時代本位主義及其不滿
大部分生活在當代自由社會中的人,在思考未來人類的發展時,缺乏足夠的評估標準,這是因為我們對於未來的看法受到個人主義和宗教懷疑主義的影響。此外,我們雖然愈來愈讚許文化多元性,卻同時對民族和種族組織的道德模糊感到不安。
儘管我們的社會與地理愈來愈聯繫在一起,但是我們對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理解卻愈來愈局限。我們愈深植現代,卻愈無法透過豐富的價值和規範體系來看待我們與我們的前人和後代之間的關係。
在本章開頭,薛富勒將逐漸崛起的時代本位主義與日益蓬勃的地理世界主義進行對比,結果指出我們的時代本位主義是我們不安的根源之一。薛富勒要論證的是,不管是出於慈善的考量,我們還是有至少四種不同的理由試圖確保後代的生存和繁榮,分別是:愛、利益、珍惜和互惠。
2.操心的理由:利益與愛
薛富勒指出,做慈善理由要不是沒有夠高的規範,就是欠缺夠強的驅動力。他說,我們有這些理由的時候,不是說每個人都有這些理由,而是許多人都有這些理由。
從實際層面來說,這個事實可以擴充我們需要的理由,推動我們採取行動確保後代的生存和繁榮;從理論層面來看,這個事實也使我們在思考我們死後那些後代生活的重要性時,能夠擁有更豐富的評估根據。
我們的關懷總是橫跨了時代,如果不能領略各項活動的跨時代面向,以及不能體會這種面向對活動的價值有何貢獻,那就不算徹底領悟各項活動的真正價值。除了慈善理由之外,還有關懷理由(concern)和利益理由(interest)。利己與愛人無法截然二分,無論我們「為自己謀利益」與我們「對後代的關懷」之間的關係多麼複雜,我們總是能區分出人類即將滅亡所直接引發的失落感,與人類滅亡會破壞我們諸多利益是兩回事。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白這些利益的損失並不能解釋那份失落感,反而是那份失落感能夠解釋這些利益的損失。因此,既然區分愛的理由和利益理由能夠有效地闡明這點,薛富勒將繼續沿用這個區分來談。
3.操心的理由:珍視與互惠
一般而言,我們不會坐視自己珍視的事物遭到毀滅;我們不會對它們的存亡與否無動於衷。我們除了希望維持自己珍視的事物之外,也會希望創造出新的價值形式和新的珍惜事物。我們不僅是保守的一群,也是創新的物種,所以有時候「保守的衝動」會與「創新的衝動」彼此扞格。
我們現有各種活動的價值,皆隱然依賴於對後人存在的信心,在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中,其實可以使用所謂「評價互惠」(evaluative reciprocity)的互惠觀念來處理我們與未來世代的關係。後人能夠存在,是我們能夠活得有價值的前提。
我們早已關心自己在時代中的地位、關心未來世代的存續。我們只需讓自己能體悟到這一點,再來就是要盡力從中推出適當的實踐結論來實行。
4.依附與價值論
這一章的目標有二。第一,嘗試將處理未來世代問題的價值論觀點與薛富勒自己提出的觀點相互比較。他的辦法主要是根據依附關係而來,但他也說過,這套主張同樣肯定我們有些關心後代命運的獨立型理由。試圖證明接受獨立的價值理由,並不能推導出我們必須尋找一套可信的人口價值論,也不能推導出我們必須找出建立在這種價值論上的慈善原則。
5.保守主義、時代偏見及未來世代
先前各章所提到的保守傾向,不是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薛富勒談的是,我們有維護或保存珍視之物的傾向,而我們珍視之物,與保存這些事物的必要方式,反倒有可能會與政治保守派所採取的政策作為南轅北轍。
如果要確認我們替後代操心的最強烈、最深刻的理由,就必須深入研究這些分歧,而不是只詳細研究中立派的慈善主張,這是薛富勒在本書中要證明的。至少,他希望能夠說服各位,除了只談慈善或主張只講慈善的觀點,或是只訴諸任何道德主張的做法之外,我們還有其他思考關於未來世代問題的路徑可循。如果擴大了視野,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本身擁有更多理由去關心後代的命運。
× × × × ×
最後,引用書衣上的這段話作為結語:「人類滅絕在即是宛如天崩地裂般的事實,這就顯示我們的自我主義有其限制,表示了我們在尋求自己人生的價值時,依賴他人存活的程度會有多高。」
註1:Q&A with Holmes Rolston: Life persists in the midst of its perpetual perishing 28 May, 2020.
註2:Zygon, vol. 57, no. 1 (March 2022)
註3:山謬‧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未來關我什麼事?》(Why Worry about Future Generations?)(2018年)。邱振訓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