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佩蓉(國立台灣文學館副研究員)
牆垣間縫隙蹦出的翠嫩小草,在風中搖曳,在磚瓦間以柔軟迎對堅硬,這是自然環境生態,也是歷史處境現實。台灣文學亦是如此,她在不同殖民時期中,面對不同強權,柔嫩的生命總是展現最堅毅的強韌。1945年二次大戰終戰,1947年二二八事件,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台灣文學反應了不同政權的樣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去,除去,切斷與遺忘戰前的文化資產;再,建造,植入與標記民族主義下的穿鑿附會。

從戰前一路書寫、研究到戰後,少數沒有被轉換的語言文字噤聲的作家楊雲萍,在〈一個誤會〉文中提到,戰前知識分子儘管努力在「民族主義」的標語下,與自中國來台者共同進行有希望的文化工作,卻仍有諸多複雜的困難,即使窮盡己力,眼前的成效還是如此有限。他這樣說:「世事是何等複雜,真理是何等深遠,我們盡了最善的努力還恐不能成就萬一。」
夾處在威權與生存的細縫,文學反映了真理與靈魂純粹的樣貌。當哲人已遠,典形消抹,那些曾經被深刻凝視、深情朗讀的文字,被塵封在政權的各樣條例、幾大建設的各種政策下。人們小心翼翼將所有疑問沒入心底,文人戒慎恐懼收起筆墨,送別繆思(Muses)。
身體不自由,心靈受苦毒,所幸,只要活著就有希望,憑藉著文學給予的盼望和力量,文人拉開抽屜,拿起筆,輕聲向心底的繆思低語:可以,我們相信總是有活下去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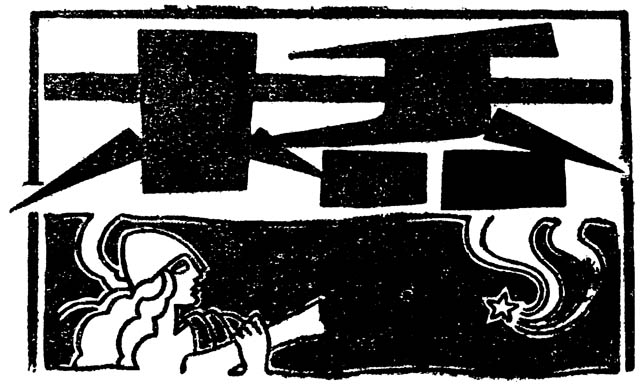
文學不死,在任何時刻,她吹動自由的靈,向社會也向人們呼喚:生命可以如何,人與人相待應該要如何。各種的衝突、萬般的情感、過去的記憶、眼前的困難、未來的可能,文學是橋,串接起各個階段,柔軟又堅強的存在。
蔡明諺老師以1949年《台灣新生報》上的「橋」副刊,為大家揭開一段台灣文學的可貴歷史:那是小草成為衝突與和解使者的見證。
相片提供/國立台灣文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