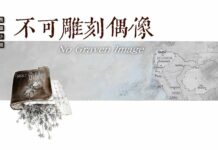和中國學生談主權
◎郭燕霖
6月5日李前總統去中央大學演講,會後有來台中國學生發問釣魚台之主權歸屬問題,李前總統答:「日本所有。」該中生又繼續逼問李前總統,李前總統則請他提出法律證據,該生無法提出。照該中生的邏輯,試問越南和外蒙古兩地,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也享有主權呢?
中生捍衛中國主權,我們可以理解,但台灣的馬政府對釣魚台主權的立場又是如何?已走入歷史的新聞局在去年12月曾發行釣魚台說帖,內容強調釣魚台列嶼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並透過教育部公函給全國中小學,通令全國各級學校加強宣導。如就目前局勢而言,台日中3方皆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該份說帖直接批判日本,但卻未對敵岸中國同樣批判,馬政府對日中兩國釣魚台主權批判力道明顯不同,令人感覺對中國似乎偏袒,是否默認中國對釣魚台有主權呢?
和釣魚台主權相比,台灣主權更顯重要。日本時代,台灣領袖林獻堂率眾抗日,但終戰後歡迎祖國的他,卻以廖文毅所創的台灣獨立黨顧問之名義,以政治難民身分向昔日抗爭對象日本政府申請庇護,此景不禁令人唏噓。對比現今陳前總統淪為階下囚,陳前總統想必更能體會中華民國政府清算之可怕。林獻堂如此,台獨運動祖師爺廖文毅更不用多說。228慘案激發廖文毅台獨意識,於是在1956年2月28日,於日本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擔任大統領一職,直接挑戰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踩到中華民國紅線,在各種威脅利誘之下,廖文毅不得不放棄台獨主張降中,卻遭到調查局軟禁,晚景悲涼。
李總統任內,台灣國臨時政府總召集人沈建德教授長期鑽研台灣主權,他主張台灣主權不屬中華民國,但其就讀實踐大學的次子沈遠弘,卻在1999年從住處不明原因摔下死亡,和陳文成命案幾乎如出一轍。沈建德高度懷疑其子死因是由於父子2人散發台灣主權傳單所致。爭取台灣主權必須付出流亡、入獄、遭軟禁或喪子的代價,可見台灣主權之爭取難如上青天,但《舊金山和約》卻給了台灣一條出路。
2009年,前日本駐台代表齋藤正樹在一場演講中表示,依據《舊金山和約》和《台北和約》,強調日本是「放棄」台灣主權,暗示中華民國對台灣沒有主權,卻旋即遭到馬政府嚴正抗議以致去職,由此可見《舊金山和約》隱藏著台灣主權真相。今「國共和談」已由「92共識」進展到「一國兩區」,中華民國政府欲偷渡台灣主權給中國政府昭然可揭,下一步當然就是殲滅台灣主權的和平協議,不過攸關台灣主權的《舊金山和約》,台灣人知道嗎?
(作者為新竹中會山腳教會會友,國小教師)
 
下雨天,留你?不留
◎周成輝
今天又是一場大雨,而且不只是一場大雨,而是一場連日來的豪雨。現在雨下的時間一次比一次久,雨量也一次比一次大,這樣的雨勢對於3年前受到莫拉克風災重創的南台灣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這一場雨,已連下數日,這些日子中落在自家鐵皮屋上的雨聲已不再是滴滴答答,而是劈哩啪啦,好似有人拿著大水桶拚命死勁的在屋頂上潑水,那樣的狠勁不禁讓人去想,這天,到底要做什麼?
過去雨天,是留客天,現在雨天,是避難日,是人禍或天災,難以分辨。雨下得太大是政府的錯?大水將堤防沖壞是老天讓雨下得太多?還是要怪我們原住民喜歡住在河邊或是山坡地,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因為天氣沒錯,政府也沒問題,發包的施工單位更是無辜,擔心工作粗重,所以意思一下,然後一下大雨,就馬上跑去躲。
政府當然也沒問題,因為當我們帶著生命家產避難時,他們要先把家人餵飽穿暖後,再著乾淨衣物體面地走進救災中心遙控災情。如果他們在中心覺得災情不夠嚴重,就會等嚴重點再救。但是如果災情太嚴重,他們也會等到不那麼嚴重再去,因為他們是政府。
這讓我想到曹丕與曹植的故事中的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若當今政府真有把他自己當做台灣人時,在台灣發生災難時,應該會以燃眉之急的積極態度,來回應災難及災後重建工作吧!當然,前提是他有將自己當作台灣人。
(作者為排灣中會傳道師)
 
有位年輕人陪我們走一段路
◎呂淑姿
在3141期《台灣教會公報》10版,一篇由洪欣萍幹事所寫的文章〈給我你的手〉,勾起我的回憶,希望藉公報一角讓大家來看看這位好撒瑪利亞人。
5月到了台北101大樓,我搭乘專用高速電梯,直達標高382公尺的89樓觀景台,迷濛細雨中的大台北對我而言是那麼陌生,我是十足「下港來的草地阿婆」,才離家一天就掛念家了,只因家中有個95歲高齡的「超級老人」。
出了101大樓,我已暈頭轉向了,忘了怎麼來的,決定搭公車到火車站。上了車,才知司機先生口中的「可以到火車站」,是該公車的終點站。
我們問他,在哪裡下車離教師會館最近,他也不清楚,這時候,有位年輕人走到我們身旁,告訴我們可以在某站下車,穿過中正紀念堂就可以到教師會館,他看我們一臉茫然,就說可以順道帶我們去。
他是上帝派來的小天使,他穿著「大安高工」的制服,我們一路聊天,得知他是建築科一年級,我問他為什麼這麼晚才回家,他說快月考了留在學校讀書,多麼上進用功!他又告訴我們,他爸爸為人拍廣告,有時候他會去幫忙,貼心又孝順,且心地善良、樂意助人。
在這個世風日下的社會中,父母或學校教導孩子要遠離陌生人,免得被欺負。這樣的教導雖然沒有錯,但如果能教導孩子有智慧,讓他們「馴良如鴿子,靈巧如蛇」,能夠判斷對方是不是壞人,也要衡量是不是自己能力所及。許多人寧可明哲保身,不願意惹麻煩,不敢幫助人,就像耶穌說的「好撒瑪利亞人」比喻中的祭司和利未人。
已經晚上8點了,這位年輕人願意付出他的愛心和時間,陪我們走一段路,就像洪欣萍幹事陪那位失明的女孩走一程一樣,我相信這位學生的父母和師長同學都會以他為榮。
(作者為台南中會東寧教會會友)
樹葬、灑葬
◎陳坤申
《台灣教會公報》3134期特別企畫的〈留住永恆的美麗〉專題非常好,尤其嘉義中會水上教會陳豐明牧師所撰述的〈落葉歸根,與土地融合為一〉一文,將主禮樹葬的經驗詳細的陳述,我相信經由《台灣教會公報》的報導,樹葬、灑葬的方法、過程應該會讓教會弟兄姊妹有所了解、認同、接受。多年前,我常與老友談起樹葬、灑葬的問題,老友們都認為在地狹人稠的台灣,尤其在大都會區,勢必要採行樹葬、灑葬。
在所有的告別式、悼念文中都會引提摩太後書4章7~8節,肯定逝世者在世的努力。經文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今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
傳道書3章19~20節說:「世人遭遇的,獸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樣,這個怎樣死,那個也怎樣死。氣息都一樣,人不能強於獸,都是虛空。都歸一處,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雖說人最後一樣歸於塵土,但若能捐贈器官甚至大體遺愛人間,那就更好。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無可避免的自然現象,欣然以對就勝過恐懼逃避。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好像一場旅行,到最後皇帝庶民殊途同歸,每個人都要死。人生百年,總須落葉歸根,若能留名青史,常活在世人心中,則可為不朽了。
從生物學來看,生命本身不具任何意義,從出生到死亡,只是一種必然的過程;唯有活得充實、燦爛,人生才有價值與意義。有生就有死,生固然可喜,死也不必害怕。前塵往事,最後都「萬千往事隨風而逝」。19世紀使英國稱霸世界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Victoria)臨終前最後一句話是:「我已盡力而為了。」
每個人善盡本分盡力而為,對人無虧欠,對事無愧疚,好好快樂的過生活,日後若能無病痛「死得痛快」,就有如《書經.洪範》篇中所說,人生有五福:「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考終命」就是「善終」,俗話所說的「好死」)──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
現代人死後的安葬,絕大部分採火化後骨灰安置靈骨塔,少部分則採土葬,捫心自問,我們五代以後的曾曾曾孫、女有什麼意義呢?是要留一個可以傳家的精神給他們呢?還是要留一罈只供祭拜的骨灰呢?美國一位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說:「心若改變,態度就跟著改變;態度改變,習慣就跟著改變;習慣改變,性格就跟著改變;性格改變,人生就會跟著改變。」
這是多變化的時代,任何事情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為不為的問題,要不要改變,存乎一心。
(作者為退休公務人員)
韓寒的文化迷思
◎陳必欣
中國有位年僅而立的網路作家韓寒,5月初來台參加論壇。回到上海後,在微博和博客上,貼上一文──〈太平洋的風〉,因為內容對台灣體驗的風評甚佳,我們這裡的媒體,甚至馬英九樂於轉述之餘,得意有加,自以為台灣真是發揚中華文化的地方。
話說韓寒,他的成就令人稱羨,「2009中國魅力榜」他入列,同年4月,美國《時代》雜誌的「全球最具影響力100人」,他也榜上有名。身為歌手、賽車手,又是網路作家,他說過一句精彩又經典的話:「文學往往是政治的妓女。」可見他觀察入微,體驗深刻,用字遣詞更道盡人人所欲言卻又難能表達者,讓讀者看到他的文字拍案叫絕。
據說在中國,不知有韓寒其人者被視為「反常」。這位公共意見的名人,當然成為年輕人的偶像。〈太平洋的風〉文中,他如此著墨:「我們的世博和奧運會,他們永遠辦不到,但走在台灣街頭,面對計程車司機、速食店老闆、路人們,我卻一點自豪感都沒有&hellip&hellip。」他認為「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他感謝香港和台灣,庇護了中華文化。言下之意,他何等期盼太平洋的風能夠吹進已經消失中華文化的中國。
每個國家、地區、文化都有其優點與缺點,韓寒提到遺失手機,被撿拾奉還;眼鏡店的老闆設想周到,為陸客解決燃眉之急&hellip&hellip台灣人的友誼、熱情、善良、誠實、好客等,我們不必否認也引以為傲,但我們也得承認,這裡相對的也有無情、冷漠、欺詐、暴力、貪婪&hellip&hellip這豈不也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或許歷史會告訴人們,香港有其可取的一面,跟英國長期的統治有關,至今多數港人寧可被英國殖民,也不願回歸。而台灣讓韓寒感動,跟日本的管轄也不能脫節。早期台灣人的守法、衛生、禮節、自制、公德心,其實都有日本的影子。可惜終戰之後,擁大中華文化的國民黨來了,這些美好的特質也迅速消失中。
看來台灣海峽兩岸仍有許多人,類似當年的猶太人領袖,認為遵行摩西律法就擁有進入天國的通行證,卻不知或故意忽略保羅是因為悔改,他的生命才產生質變;他得著救贖不是來自律法或文化,而是他找到了「真理」。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祈願大家找到正確的道路,擁抱真理,從而生命得到更新,不要再陷入任何的文化迷思。
(作者為高中退休老師)
成功神學的自我實踐與自戀文化
◎王樵一
今天世人很可能正被包裝得很漂亮的「自我實現」所蒙蔽,誘導遠離神,高舉自己的墮落沉淪之路而不自知,甚至部分主內弟兄姊妹也相信,自我實踐的自己是活出神的旨意的美好。
加拿大哲學家暨政治學者查爾斯.泰勒曾指出,當代社會「自戀文化」的一個重要展現方式,就是以「自我實現」做為日常生活的主要價值,而且很少願意承擔外部道德要求或者對他人的嚴肅承諾。
舉個最常見的例子,個人主義的自我實踐讓人寧可選擇拚事業而放棄結婚生子。人們不願意因為生孩子而放棄目前的生活水準、事業上可能的升遷,都因為那可能拖累自己,使得自己的人生無法自我實現。不顧外部道德成本與對他人承諾的自我實現,其實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泰勒認為這是自戀文化的具體展現,僅僅是一種自我放縱和利己主義的表達,不受任何理想的驅動,更要命的是假裝成自我實踐的自我放縱,也就是享樂主義。
自戀文化藏在自我實現的美好理論裡,偷渡到當代社會的生活中,以勵志、學術、宗教信仰、人生哲學、同儕壓力、廣告行銷等各種各樣的方式鼓勵人們信奉。然而,自戀文化就是人類自我中心的展現,正是聖經中所說的罪,驕傲的自以為義,高舉自己,將神、社會、他人等排除在外,只要求享受權利卻不願意屢踐義務。自我中心高舉自己,視自己的需要滿足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自我實踐成了自我合理化此一論點的最佳包裝。
企業只在乎利潤最大化,政客只在乎自己能否選上,每個人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擴張自己的境界,至於擴張境界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對他人的傷害,全都不在自己的考慮之內,更別說幫助社會的窮苦大眾。在自我實踐的面前,一切社會責任退位,當自我實踐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時,也讓人成了最自私自利卻又有自我合理化的藉口。
而今,自以為義的自我實踐開始偷渡到基督信仰之中,以成功神學之名鼓勵弟兄姊妹追求個人成就的極大化,追求人生的自我實踐,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理想,甚至告訴弟兄姊妹自我實踐是神的美好旨意。
成功神學暢談個人生命的豐盛、活出美好,告訴弟兄姊妹越虔敬者越能賺大錢、在教會的地位也越高,卻不談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也不談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不談約伯那無來由的全然承受苦難,不談基督徒做在最小的一個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的社會責任,信奉自我實現的基督徒不斷累積世上的財富,卻對鄰里餓死的窮人不聞不問。
自我實踐若不能伴隨著愛鄰人,不能成為好撒瑪利亞人,反而成為剝削結構的共犯,那恐怕便落入假裝成天使的撒但陷阱,自以為信奉耶穌基督,其實則是追拜瑪門去了。
難道你能相信,耶穌允許你擁有龐大的財富是為了炫耀,而不是為了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弟兄姊妹這樣荒謬的事情嗎?耶穌呼召我們悔改,是做祂的門徒,做能夠改變世界的光和鹽,倒空自己,成就福音的小基督,不是為了拚命賺取財富與聲望而不顧一切的(偽)自我實踐者。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全職服事,念神學院較好
◎余茂洋
這時是各神學院招生的季節,要不要在人生中放下工作,進入神學院?決定念神學院是非常大的改變,許多人為此觀望、猶豫、準備、拖延多時。一般不念神學院的有以下理由:
1.所學非所用。神學生畢業後,發現教會、福音機構所要的與神學院學到的有落差,教會的需要主要落在「如何做」,像如何讀經、如何禱告、如何帶青、少年團契、主日學、小組等,弟兄姊妹不在乎解經是否正確,他們所要的是這段經文能帶出什麼祝福,如何處理他們每日問題。
2.受前輩影響。教會服事的傳道人推波助瀾,說神學院所教的東西沒有用,平白浪費幾年時間在封閉的神學象牙塔裡,教會所需要的神學院沒有教,神學院所教的教會幾乎用不到,冷卻人想念神學院的心。
3.可行第3條路。有人認為花幾年念神學太長了,不如一邊工作一邊當選修生,魚與熊掌兩者兼得。何況邊工作邊修學分,馬上學以致用,進可攻退可守,何樂不為?
4.誤解知識教人高大,惟愛心能造就人。誤認知識定與愛心成反比,只要會禱告,帶犧牲的愛和關心,不必管他講的內容來自加爾文、約翰衛斯理或其他人,不必管與上下文關係通不通,是不是自己亂解釋,只要藉著各種聚會,人數可增多,幫他們解決問題,目的達到即可,過程是否合乎聖經不需要考慮。
實際投入服事後衝擊更大,有隨從後現代主義講求多元,以「市場」當導向,人們需要什麼就提供什麼;有排斥傳統,認為只要可行,各種嶄新方法都行,怎麼做都不要緊。另一種極端是緊抱著聖經,台上忠心講聖經,只處理教會圍牆內的事,缺乏把信仰落實在生活中動力。
最好的選擇是聖經怎麼說,人就怎麼做,若不清楚明白,就暫時把它放著,直到見主面,可以面對面清清楚楚問祂,到底這是什麼意思,要如何做。畢竟隱祕的事屬於耶和華。(申命記29章29節)
「當竭力成為上帝無愧工人,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是全時間服事上帝者的職志,一切問題都是解經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要念神學院的答案。藉著學有專長教師,學得廣闊、平衡的聖經知識層面,及如何用在日常生活的技巧,針對時局採取適當的對策。
藉著住在一起學習同心服事,彼此扶持成為團隊,讓上帝修剪性格;藉著週末實習,享受聖靈能力,把所學落實在各種服事上。藉宣教實習,知道教會不光是為自己周圍的社區存在,是為上帝國存在,心胸寬廣,關心本土,同時關心「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做上帝的見證」。
神學院訓練絕對不會、也不可能解決教會、福音機構的所有問題,但肯定能提供像蓋房子第一步驟&mdash&mdash堅固的鋼筋水泥基本骨架,它不好看,然而在上面建造,貼磁磚、隔間、粉刷、精工細雕等,美侖美奐的房子就彰顯出來。選一間正統、圖書設備夠、教師學經歷足的神學院,自己清楚上帝的召命,把身子擺在那裡學習,上帝呼召祂必定負責。
(作者為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牧師)
現代詩:醒、悟
醒、悟
以精雕塑
關於季節
盛開一朵各自的姿色
晨偎
夕眠
春眉
夏唇
秋耳
冬頸
還有比這樣的塗寫更
雄厚的纏綿?
更雷雨大地
風火生息?
我們
七彩繽紛是因為
神十字架上再生之
眼 擁生不息的
光明燈
傳給人、傳給人、傳給人
提醒自己 救恩之美
*
眼=重點,如詩眼。浩瀚的思想與目標
關懷牧家孤兒
◎ 賴信瀚
近年來,長老教會有許多牧者在正值壯年期間驟然別世。這些壯年別世的牧者,大多留下許多未成年或就學子女,這些牧家孤兒不僅失去天倫之樂,在生活上也頓失主要經濟來源,若未能得到支援,生活處境堪憂。大多數牧師待遇並不優渥,除非牧者本身繼承來自家族的龐大遺產,否則當一個人獻身走上傳道之路,他的人生也就和經濟上的富裕絕緣了。因此當牧者在壯年別世,遺族必陷入經濟困境。他們是我們的肢體,需要我們關懷。
我們所領受的福音是愛的福音。約翰壹書4章16節說「上帝就是愛」;3章17節也說「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我們教會小會看見這些牧家孤兒需要,經過討論,決定喚起兄姊對這個事工的關心,也促使我們藉著實際的行動操練信仰。因此,小會決議在大齋節期第一個主日為牧家孤兒的需要奉獻和代禱。
早期教會的傳統,要求信徒在大齋節期間嚴格守齋(每日只吃一餐),藉著禁食來操練信仰。禁食的意義不僅在吃喝方面,也在眼目和五官的守齋,與基督一同克己受苦,經歷試煉和得勝試探。藉此一方面操練自己的靈性,體會與基督一同受苦;一方面也能體會饑餓與貧乏者的痛苦。大齋期將所省下來吃喝玩樂的錢,用來幫助饑餓貧困的人,或支持福音事工。因此,在這個主日關懷這些牧家孤兒的需要,和我們的信仰精神是極為切合的!
上帝雖未曾應許天色常藍、花香常漫,但祂為我們預備了彼此,使我們可以成為互相的幫助與祝福。人生道路坎坷漫長,還好我們擁有彼此,當我們軟弱時,還可以得到扶持;當我們陷入困境,還可以得到幫助。因為我們擁有彼此,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因此充滿了上帝的恩典。
(作者為台南中會大同教會牧師)
上帝真會捉弄人?
◎好是123
「上帝真會捉弄人,像這樣的人,居然還有性慾!」山本清子在協助《性義工》的作者河合香織在荷蘭採訪身心障礙者談性/愛需求的處遇時,這樣感嘆。美國紐約法學院教授麥可.波林(Michael L. Perlin)在長達數十年鑽研身心障礙相關法律問題的過程中,發現「這樣的人」所渴望的,遠比一般社會所能寬容或體諒的要來得多,舉凡婚姻、性與生育,無一不是。
當身心障礙者的期待與社會認可的尺度出現落差,身心障礙者的弱勢處境使他們的自主意見往往被「『理』所當然」地忽略。講到婚姻大事,父母常出於照護的考量,為他們的婚或不婚作安排,不是娶外籍新娘、找老榮民嫁掉,就是直接安排手術,從此一勞永逸。少數的例外,如障礙不太嚴重的視障、聽障,以及侏儒症患者,若想要天生自然,或藉助人工生殖技術有個「相似度百分百」的孩子,動輒會遭斥責「無『理』取鬧」。至於性,對於24小時住在安養機構,或身心缺損、社會排除因素而不便自行到位的障礙者,就成為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理』該如此」施以規訓與懲戒的少數社群。
身心障礙者的婚姻、性與生育,在社會福利政策中不是自動消音,便是視為禁忌,這皆與社會所認定的「理」,特別與身心障礙的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身心障礙者不是被視為「無需求」的「中性人」,便是以「不要吵醒沈睡中的孩子」的方式「去需求」;再不,便是被當作「過度需求」的主體,藉由宗教、教育、醫療或法律嚴加管束。
這些關乎身心障礙者切身的處遇,多虧聯合國2008年實施的《殘疾人權利公約》,揭示「締約國應當採取有效和適當的措施,在涉及婚姻、家庭、生育和個人關係的一切事項中,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消除對殘疾人的歧視。」身心障礙者才是權利的擁有者,用身心障礙運動的口號來說:「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殘障解放神學家依莉沙白.史多特(Elizabeth Stuart)指出,身心障礙是「被壓迫者中的被壓迫者」,如果基督教是「道成肉身」的信仰,那麼「身體很重要!」這不但讓我們反省肉身的不穩定,更迫使我們正視文化中的身體政治,促使我們省思如何建構讓所有身體都得以參與的「基督的身體」教會。
正視身心障礙者需要,並同他們對話,是教會從事殘障本土神學的使命,6月16日「算障與爭權:談身心障礙者的婚姻、性與生殖之天賦人權研討會」(333dtonline.blogspot.com),更是參與殘障解放運動的起點,歡迎參加。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